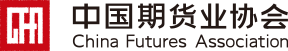主持人: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 郑学勤
讨论嘉宾: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 Phupinder S.Gill
欧洲期货交易所执行董事 Michael Peters
新加坡交易所执行副总裁 周士达
香港交易所总裁 李小加
台湾期货交易所董事长 刘连煜
郑学勤:我们在不同的全球会议上多次见面了,既然来到这里,还是对中国市场做一些展望吧。我们知道中国商品期货市场上很多品种已经是第一位了,股指期货是第二位,发展很快。中国的期货公司也开始转型为期货佣金商和财富管理公司,很多企业意识到真的需要一些工具来管理风险。
再过十年,也许中国期货市场将会成为一个全世界都瞩目的市场。中国不是一个旁观者,将会积极投身于国际期货市场当中,中国迫切需要了解外界,也希望从各位身上学到经验。我先问第一个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市场发生很多变化,对其他市场也产生连带影响。此后引发的改革相当复杂,包括多德·法兰克法案。在你们的印象里,金融危机后发生的哪些重大金融改革令你们感受深刻?同时,对于CME或欧洲市场,我们要关注什么?现在法规如果改变的话,我们应该留意什么?
金融危机后境外OTC市场监管改革
Phupinder S.Gill:当我们谈到国际期货交易所的发展历史,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也反映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沿革。比如,对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债期货事件,我认为中国采取了非常坚定的做法,重启期货交易所体系,让它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证监会也确实推进了这些发展,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市场。在发生很多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转折点,国债期货事件是其中一个转折点,市场重新开放又出现了新的转折点,特别是自贸区的出现又是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在2000年交易所公司化以后,从会员制转向股东制,其实没有改变它的重点,重点还是风险管理,还是服务实体经济,宗旨也没有变,还是确保价格发现、市场公平。2008年这场场外危机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转折点,CME自此转型,从一个期货期权市场转变为一个金融衍生品市场,包括指数掉期也可以在我们这里挂牌交易和清算。现在我们看到几十亿的保证金,2008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在欧洲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市场的透明度、流动性都成为非常关键的因素,不仅是对场内市场,也包括对场外市场。
郑学勤:金融监管政策改变很大,欧洲有6万多页的法律条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其实他们的市场进步了很多,虽然监管复杂了很多,但在中国他看到同样的。现在市场越来越关心流动性,不仅是价格问题,有没有流动性,也包括风险控制,因为大家需要风险控制,而且他们把OTC吸收到这个市场中来。你觉得十年以后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市场机遇?
Phupinder S.Gill:我们觉得一切都可以清算,有些市场也愿意接受清算。但关键是法律的要求,法律是非常复杂的,哪些是交易的,哪些是清算的,法律界定还是比较清楚。我们其实可以对任何可以清算的交易进行清算,但不是所有交易都做好了清算准备。我觉得十年之后将会有很大一部分市场进入清算领域,我们会看到很多交易所,包括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交易所,都会投身于我称之为组合优化的过程。
郑学勤:问一下新加坡,新加坡也在中央清算场外产品。在场外产品的清算方面,你们现在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进展?
周士达:刚才你也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监管当局都要建设比较健康的管理环境,欧美出了很多新条件,这些条件都很复杂,对新加坡也有影响,因为我们的客户都是比较国际化的客户。前几年,我们努力修改完善交易所规则,可以顺利地跟欧美等国家说新加坡有一个很健康的环境,在场外交易或场内交易方面,我们可以协助欧美等国际投资者。2013年12月,我们成为亚洲第一家美国确认的交易所,我们也要更加努力地协助国际投资者。
郑学勤:小加,我知道你们在沪港通方面有很多成熟经验,在OTC方面有什么动作吗?
李小加:允许我把这个问题展开一下。实际上,目前内地期货市场和国际期货市场在监管方面完全是两个极端。
过去这么多年里,由于长时间的低利率和便宜的钱的泛滥,最后造成大的金融危机。OTC市场基本上是浑浊的、看不清的,但是非常赚钱,这里面问题很大。对于OTC市场,第一,能不能至少做到透明,每个国家都必须建信息库;第二,稍微能够有标准的合同就一定要在清算所清算;第三,只要能够在交易所交易的必须进入场内交易。
同时又对很多金融企业的基准价格加强监管,以前是人管的,几个金融机构在一起基本上是公平的,但是每天都一点点地不公平,出现了很多丑闻,这就要大规模压制,然后监管。现在又对整个价值链里的很多标准进行监管,比如我们买的LME的仓储,它认为有些企业不能上游也管、中游也管、下游也管,把标准搞乱。
这一切的监管都是从流动性、透明度、资本安置方面开展的,把互相的债务链清算掉,不能交易的清算,不能清算的报告,不能报告的最后在资本上全面地做出要求。这样一来,整个金融界特别是期货界成本剧增,相比以前资本不那么低、不那么不透明、不那么不好的情况,现在稍微赚得少一点。
中国的监管和国外的监管实际上是反过来了,中国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系统性风险,现在主要是落在个体上的风险。对于一个监管者、一个市场基础设施、一个交易所来说,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如果你自己倒了别连带着大家都倒,而会不会把股本金都丢光了是你自己的事,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企业。
郑学勤:小加,我打断一下。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OTC市场,应该重点发展场内市场?
李小加:不是这个意思。有些合同能够在场内做就在场内做,不能做的要去中央清算,实在清算不了的,至少要有透明度。
郑学勤:Gill你呢?
Phupinder S.Gill:我想补充一下李小加刚才所说的内容,就是说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放到中央清算,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监管环境是不一样的。中国市场比较封闭,在这种市场中,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来资本充足率现在已经酝酿到非常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对于债券市场或其他市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能够更好地确保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我想在这一点上其他市场是没有可比性的。
郑学勤:小加提出的观念很重要,中国市场和西方市场不一样,不能照搬外面的概念。中国本身的OTC市场不是很大,不能照搬西方的监管方法或发展方法来直接发展我们的OTC市场。OTC市场一定会有,因为它有很多自己的功能,透明性和流动性是特别要关心的,这是他们俩的观点。Michael,您要不要讲一下欧洲期货交易所在监管方面的变化?
Michael Peters:我非常同意李小加的观点。我们增加了OTC市场的质押比重,在OTC市场我们需要对资产进行分级,不同的资产分级有不同的监管方法,我们不会“一刀切”地全部都是标准化合约,我们会看到OTC市场的具体要求,然后根据具体合约实施相应的清算标准。
第二,我们在监管方面的改革方向也是对资本金有更高要求,尤其是衍生品市场中的资本金。就像刚才李小加所说的那样,我们有中央清算,但是并不意味着什么东西都要进行中央清算。我们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些更加灵活的清算机制,依据具体的合约、清算需求,选择不同的清算机制,我想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要求。就是说在清算上面可以做到更加灵活。
第三,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过渡阶段。
期货市场应回归和服务实体经济
郑学勤:过去几年间,大家公认西方金融监管越来越严,可能有些过于严。从中国角度来说,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就是期货市场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从交易量、管理需求等方面考虑的话,衍生品市场如何更好地回归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Phupinder S.Gill:我们主要是这样考虑的:第一,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是什么;第二,衍生品市场买家和卖家的兴趣是什么;第三,在衍生品市场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例子,我认为失败的要比成功的例子更具有学习的必要性。我们从市场当中看到那些失败的案例,很可能是合约的原因,或者是合约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卖家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考虑这些综合因素。
Michael Peters:我想补充一下。我们要考虑衍生品市场和风险管理机制之间是否相辅相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价格发现机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在经历欧元危机时,看到了套期保值带来的保护作用,一些国家很有效地运用了套期保值,最终他们的信用发生了正向变化。我们在期货市场或更大的衍生品市场,当然要跟踪产品价格走势,然后才能做出判断。我觉得衍生品市场是一个很好的风险转移市场,如果对实体经济的产品有很好了解的话。
郑学勤:新加坡设计A50这样的产品有什么样的考虑?
周士达:我们要做亚洲金融衍生品门户,我们跟CME也有合作,所以设计出的产品都差不多,Gill本身也是新加坡人。我们怎么去设计?刚刚提出的问题是关于OTC的,前两三年我们推出了OTC铁矿石掉期产品,推出之前当然要考虑它对客户会有哪些好处,中国的铁矿商和螺纹钢商都有需求,新加坡投资者也有需求。我们的考量是以客户为重的。
在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之间保持平衡
郑学勤:小加,你们现在的战略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全球性战略。你们现在要做期货产品,在中国并没有很多生产商和使用商的情况下,发展这个产品到底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好处?
李小加:我暂时不说港交所,还是回到刚才的主题——市场结构之间的区别给我们什么启示。国际市场以前非常活跃、非常大,水很深、很浑,营养非常丰富,然后鱼很大,实体经济也是大头鱼,无论是生产商、加工商、贸易商,还是银行、基金,都是很大的鱼。但是水非常浑,监管者看不到底。在这种利率特别低、资金泛滥的情况下,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巨大的。但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无可厚非。
反观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已经早早地被拿掉了。我们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市场,没有这么透明的市场。我们的保证金都是统一的,而且比别人高很多。我们的一系列监管都已经在软件系统里面了,非常安全、透明。期货市场本身应该更多为大户服务,但我们实际上是以散户为主,期货公司也长不大,监管者对于保护投资者的理念也非常强。但是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鱼池太干净,只能养点小鱼,这是个问题。
那边太浑了,一定得改,在赚很多钱的情况下改革。我们这边怎么能够让期货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实体经济,在期货市场真正充分地对冲风险?我倒是觉得我们这边更应该扶持大家的创新力、提高大家的存活率。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大宗商品的最大生产国和进口国,在受到世界价格制约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跟大鱼池接轨,一定要跟大鱼打交道。
我特别高兴看到国际化的原油期货马上要推出。现在美国施行“长臂监管”,只要是美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业务都要管,用美国的标准、法律来管。香港是个开放的市场,欧洲公司在这儿,美国公司也在这儿,美国公司要受美国监管,欧洲公司要受欧盟监管。我得老老实实地符合美国的规则,也得跑到欧盟那边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只有这样,我的系统才能让全部大金融机构交易。
内地短期内很难让美国、欧洲监管,也就意味着很多国际大行不能把钱拿到中国来,也不能够加入我们的清算体系。我最后做点广告,香港短期内可以给大家做这个事,我们配合内地交易所。LME每天的交易量和持仓量是一个三角,底下是持仓量,上面是交易量,底下是实体经济,上面是交易者,中间是实体经济的服务者,而内地交易量和持仓量是倒金字塔。我们就在想香港打出个平台来,利用这个平台跟内地期货交易所合作,把两个金字塔并在一块儿就是方的了。
郑学勤:小加,那我提个问题。如果监管那么复杂,要受全世界的监管,到你那儿交易不是很复杂吗?
李小加:我受监管的意思,不是说我来管别人,而是说,到我这里交易的人因为我受他的主人监管了,他才能到我这里。比如花旗银行到我这里的第一个条件是我受不受美国监管,我说受,他就来了。
Phupinder S.Gill:中国有这么好的机会,有这么出色、合理的系统,而且美国的规则有很多不太合理的要求,实际上欧洲的监管也是非常严格的。中国应该做一些简单正确的事情,同时还要不断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一定要跟上,这样中国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中国面向世界的时候,香港是一个好起点。
台湾期权交易经验分享与借鉴
郑学勤:刘理事,我们知道台湾期交所的股指期货和期权对台湾股市起了很好的支持作用,能不能介绍一下经验?
刘连煜:台湾的交易量现在世界排名第六,根据最新统计,我们一周到期的交易量在10月底时已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一。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时主要是贴近市场需求,刚刚各位讨论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到其主要目的就是预防金融性风险、保护消费者,我们也重视这个。所以除了贴近市场需求外,我们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有要求的,因为台湾的交易人50%是散户,主管机关非常重视交易人的保护。
为什么周到期的交易量会蓬勃发展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它的存续期间比较短、交易成本比较低、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引来的交易人比较多。另外一个例子,台湾的交易时间是比较短的5个小时,从早上8点45到下午1点45,为了延长交易时间,我们跟欧洲的一个交易所连接在一起,成效非常好,我们的交易时间就可以涵盖欧洲交易时间、美国交易时间,变成18个小时。
期货市场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这也是台湾期货交易所的愿景,我们要靠期货交易来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台湾期货交易所跟欧洲交易所的链接,把台股选择权、台股期货挂在欧洲,把期货商品出口到国外,因为贴近市场所以可以服务实体经济。
各国对衍生品的监管目前还没有一致,因为各地区有自己的市场和文化。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改革、融合、竞争,台湾期货交易市场有个产品跟新加坡几乎一样,这两个市场如何竞合?台湾市场基本是散户50%、法人50%,但是新加坡市场9成都是法人。这两个市场均以台股期货作为标的,是有重叠的。因为彼此有价差,所以两边市场交易人可以进行套利交易或者价差交易。所以,我觉得虽然监管不一致,可是也会形成商机,期货商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从事两边的价差交易。
郑学勤:台湾期权出来以后,期权交易量和期货交易量的比例怎么样?
刘连煜:现在交易量大概1/4是期货,3/4是期权,2014年已经突破了历史最高交易量,即将到2亿口。
郑学勤:为什么期权交易量比期货高得多?
刘连煜:我们叫选择权,以散户自然人为主,把企业规格缩小,吸引他们进来交易,交易成本也比较低。交易的手续费也只是期货交易的一半而已,可以增加散户交易的意愿。
郑学勤: 大陆很快就要推出期权了,台湾推出期权时,在风险控制方面,在散户占主导的情况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刘连煜:前几年因为发生了违约情况,我们就推出了两个机制,风险管控机制,还有申报。我们曾经在两年前发生了一个大案子,出现了巨额违约情况。因为当初法律定得不清楚,主要规定是要不要把它冲销掉,曾经在法令上是用的,期货商就把这个规定当成市场工具,你已经亏损了,保证金不够了,我们就可以卖一点冲销掉。我们痛定思痛之后,联合主管机关把法律定清楚,什么情况下应该代为冲销,就变成强制了,实施以来非常好。
另外,我们在申报方面也做得很好,每天检视交易人的风险,对其账户安全加以分析,如果损失可能超过一千万新台币,我们就会注意。我们在散户风险管控上着重做到这样两点,实施以来成效非常好。
周士达:刚才刘总也说了新加坡和台湾期货交易所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已经有18年历史。两岸的期货和现货市场合作前景比较广泛。刚才有嘉宾也谈到中国在监管方面当然要走自己的路,新加坡是个小岛,没有办法不以顾客为重。
高频交易对期货市场的影响
郑学勤:下一个议题是境外成熟市场高频交易经验借鉴。
Phupinder S.Gill:我觉得高频交易肯定要上升30%,不会超过30%。
周士达:高频交易差不多20%吧。
李小加:我们没什么高频交易,在一个收印花税的市场里没有高频交易。
刘连煜:台湾期货交易所有制度,交易人不会直接连线到交易所,所以也没有高频交易环境,我们现在也没有提供主机服务。高频交易比例大概是12:1。
Michael Peters:其实每一位嘉宾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观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能这才是最重要的。
Phupinder S.Gill:高频交易意味着交易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这样高的频率没有真正考虑到市场的变化,当然市场是千变万化的。我们要考虑高频交易产生的原因,也要看其对市场能不能带来价值。我们要非常小心,每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必须了解监管需求。
郑学勤:我们看到国内外交易所没什么太大区别,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好,注意流动性、透明性也好,最大的区别主要是监管。中国的监管环境没有必要完全照搬美国,因为我们已经站到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实体经济。
总的来说,我们的市场离国际市场越来越近,但是要到别的市场交易就必须学会人家的规则。我们未必要照抄人家的规则,但透明性、为实体经济服务、流动性这些因素都是必须要注意的,包括高频交易。高频交易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什么是高频,什么不是,到底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具体的市场。
(本文根据会议记录整理,略有删改,未经本人审阅)